在清朝光绪初期,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特大旱荒。北方五省——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、山东,以及苏北、皖北、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均受到波及。这场旱灾的破坏程度极其严重、深远,史书中罕见,共有1000多万人遇难。这场旱灾被称为“丁戊奇荒”。
灾荒之时,清廷没有完全从国内战争的糜烂之局中恢复元气,边疆危机又接踵而至。荒区内,成千上万的饥民、流民以及此灭彼起的闹荒、民变,使略趋平静的局面动荡不宁。
内忧外患,交相煎迫,清廷似乎朝不保夕。
为了稳定统治,清廷采取蠲免赋税、散放钱粮、设厂放粥、设局平粜及以工代赈等一系列荒政措施,赈灾安民,不可谓不努力。
然而,这一传统救灾方式起到的效果却并不称得上好,与风起云涌的“义赈”(近代工商业者如江浙绅商组织和发动的民间赈灾事业)相比,黯然失色。
战争结束后,北方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依然沉重。“农民终岁所入,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,实无所余,甚为赔累”,有时连“种粮尽粜卖以应追呼”,生计日窘,即使正常年景也难资糊口,一遇荒歉,立即陷于饥馑流离。时人谈及奇荒与赋役,痛切地指出:“饿殍见于既荒之际,饥溺已形于未荒之年”。

陕甘总督左宗棠反复强凋“恤贫以保富为先,办赈以遏乱为急”,“荒政救饥,必先治匪”,并不断提醒陕西巡抚谭钟麟“办赈须藉兵力”,对“藉饥索食、仇视官长”的所谓“匪类”,“非严办不足蔽辜”。于是,铤而走险的饥民、流民无不惨遭屠戳,地方豪绅奸商则有恃无恐,纷纷乘灾打劫,更加深了灾难。

救荒之时,清廷内部派系之争日趋尖锐,皇室纷争不己,督抚各自为政,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,或遇利必争,或遇事推诿,明争暗斗,风波靡定,统治机构运转失调,行政效率大为降低。
这种情况不可能让救灾走上统筹规划、协调一致的轨道。诚然,在清廷督导之下,被灾各省不少督抚大员勤于赈灾,不辞劳瘁,但往往自顾不暇,各自为战,灾轻或无灾省的封疆大吏除少数心存利济、热心支持外,大都作壁上观,对于清廷支援灾区的谕令,囿于畛域之私,或拖延搪塞,或大打折扣,从不认真执行。
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
外国资本主义不光输入了鸦片,还输入了“现代”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,特别是《北华捷报》中关于“丁戊奇荒”的报道,反映出其信奉的自由贸易及放任经济。这与中国传统官赈做法相矛盾。
当时,印度和爱尔兰的特大饥荒与“丁戊奇荒”几乎同时发生,但英国在两地的决策人及赈济官员坚持不干预,拒绝国家对养活人民应负家长式责任。那时,英国认为受灾地的穷人懒惰而过度依赖,难民应致力于公共工程项目,以换取食物或勉强糊口的工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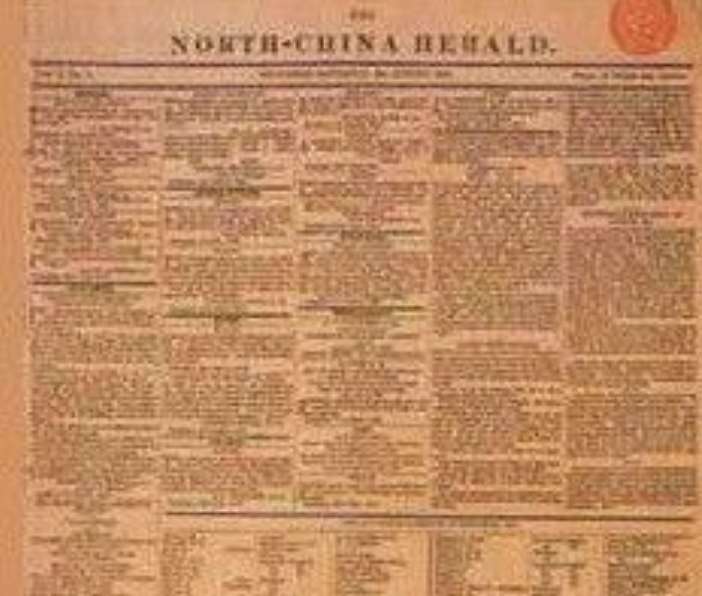
英国编辑们对清廷免费为饥民发放食物及现金大惑不解,认为“丁戊奇荒”之所以发生,是因为缺乏科学、铁路和资本主义经济,指责北京“统治者官僚”“将一场严重的匮乏加剧为饥荒”。
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
平心而论,针对丁戊奇荒,清廷组织的赈灾,时间之长,地域之广,数量之多,堪称史上之最。同时,作为传统荒政在近代史上的大规模实践,赈灾又多多少少打上了近代文明的烙印,渗入了不少诸如海外侨胞的输捐和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新的因素。
传教士李提摩太赞美了清廷的赈灾工作,“与中国政府本身的工作比起来,外国人的努力最多不过是桶里的一滴水。在豁免税务和直接给予山西赈济之中,它至少给予了200万英镑。”他们赞扬了清廷在饥荒区域禁止罂粟种植的努力,将饥荒看作对英、中两国的教训,并批判了英国的一些对华政策。
但是,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破坏力量,清廷的赈灾实际只是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,又因为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“现代性”开放,清廷国家生产力、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迅速下降,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,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动荡的冲击下,仓储又发生灾难性损耗,朝廷,再也无法像18世纪的盛清那样赈灾了。
